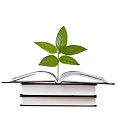一、埋头狂奔
2021年9月6日,千味央厨敲钟上市,首日涨幅近44%。接下来的十个交易日,千味央厨天天涨停。短短11天,股价就暴涨了310%!
说起来,千味央厨只是一个成立不算久,主打卖芝麻球等米面冻品的食品小登。当年茅台打出这个战绩,用了整整六年,而“寒王”寒武纪,今年也只涨了140%多而已。
为啥卖芝麻球的,比白酒和芯片还猛呢?
招股书显示,2017-2019年,千味央厨营业收入分别为5.93亿元、7.01亿元、8.89亿元,复合增长率22%;对应净利润分别为0.47亿元、0.59亿元、0.74亿元,综合毛利率不超过25%,随便拉个食品龙头来比,千味央厨都显得很普通,受资本追捧,主要是因为叠了预制菜的BUFF。
千味央厨上市的几个月前,有个业绩更普通的味知香,凭借“预制菜第一股”的光环上市,狂揽10个涨停。千味央厨总不能叫“预制菜第二股”这么low的名字吧,只好换个横幅,叫“餐饮供应链第一股”。
当年抄底抄在半山腰的大A韭菜应该还记得,2021年下半年,消费股已经开启了震荡下跌周期,老登消费股被暴打一顿,唯有小登预制菜股扬眉吐气。
不过,对于李伟来说,一切都在计划中,基操勿六。
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于河南驻马店的李伟,是中国冻品巨头思念食品的创始人,也是千味央厨的创始人。
之所以要聊这个公司,不仅是因为它是做预制菜的,更是因为从思念食品到千味央厨的演进过程,浓缩了中国预制菜的进化史。
1997年的河南,速冻食品行业正在从萌芽走向狂飙。
为什么要特别强调速冻食品呢?
从美国和日本的经验来看,两国的预制菜巨头,早期都是做冷链食品发家的,后来凭借冷链优势,拿到连锁快餐店的订单,从而丝滑切入预制菜。
如今年销售额500亿美元的美国预制菜巨头Sysco,就是1969年,搞冷链餐食配送的公司Zero Foods,和另外八家食品公司合并的。
日本的预制菜巨头日冷集团,其前身是“帝国水产控制株式会社”,二战时专门给日军运送冷冻水产的。
所以,河南作为中国速冻食品产业的摇篮,自然会孕育出预制菜产业。
河南最先萌发冷链物流系统,是因为河南是九省通衢,又是农业大省,最早聚集了一批现代食品加工行业和物流企业。
运输冷冻产品的市场需要,刺激河南诞生了强大的冷链物流产业,进而萌发预制菜产业。
在《2025年中国预制菜企业百强榜》中排名第一的双汇集团,前身是漯河市冷仓,改革开放后最早引进了先进冷鲜肉加工线,双汇物流也是全国顶级的冷链企业。
1992年在郑州成立的三全食品,早先靠卖冷冻汤圆发家,是中国速冻行业的教父级存在。
1997年,李伟为了“三年超过三全”,梭哈了借来的200万,在三全汤圆厂对面,怼脸开了一家思念汤圆厂。
2001年,郑州人刘鸣鸣也想进军速冻食品行业,但三全和思念在河南杀得过于凶残,刘鸣鸣便去福建猥琐发育,2001年开了一家冻品公司,主要做冷冻鱼丸,这就是另一家冻品巨头安井食品。
河南人在中国食品界真是彪悍的存在,中国排名第一的肉类加工厂是河南人开的,排名第一的奶茶连锁店是河南人开的,三大速冻食品巨头还是河南人开的。他们以各自的方式,静静地推动着预制菜的齿轮。
1992到2010年,中国经济一路狂奔,所有人都忙着创业、上班、聚会、唱K,越来越不愿意在家花两个小时做饭,速冻食品行业迎来迅猛发展期,思念、三全、安井也长成了中国速冻巨头。
2011年后,速冻食品行业进入缓慢增长期,行业大佬意识到,这块蛋糕已经做不大了,必须切换赛道。
于是,思念、三全、安井纷纷决定进军预制菜,不过由于创始人性格不同,大家的操作也各不一样。
三全创始人陈泽民保守稳健,强调稳扎稳打,而李伟擅长资本运作,思念显得“玩得很花”。
思念2006年在新加坡上市,融资约20亿元人民币。2012年,思念股价从发行价的0.54新元跌到了0.13新元,李伟启动私有化退市,只花了约6亿元人民币,中间差价达到14亿,操盘水平可见一斑。
思念退市这一年,李伟创立了千味央厨,从名字就能看出,李伟是要进军中央厨房。就在千味央厨创立的前一年,中央文件首次正式提出“中央厨房”概念,这个热点,蹭得妙啊。
当时三全已在国内上市,股价涨得很好,市值达到了思念的四倍。但李伟不紧不慢,打算依托思念的厂房和营销体系,带飞千味央厨。
此时思念已经是隐藏的预制菜大佬,早在2002年就成为肯德基蛋挞皮的供应商,2006年开始又为百胜中国(肯德基母公司)研发和供应油条。
李伟只需要把思念大客户的核心业务,倒腾给千味央厨,千味央厨就能原地起飞。
千味央厨成立第一年,就成为百胜中国的供应商,接着又拿到了赛百味、华莱士、真功夫、老乡鸡、永和大王、九毛九、小龙坎、杨国福麻辣烫等餐饮连锁的订单。
2015年,李伟准备推动千味央厨上市。但监管机构认为,千味央厨和思念集团关系不清不楚,疑似存在同业竞争或关联交易,这意味着千味央厨想要上市,就必须同思念切割。
李伟会选择谁呢?从账面上看,千味央厨高速增长,思念却在原地踏步,简直是道送分题。2017年,李伟出让了思念股权,退出了思念管理层。
次年,京东对千味央厨进行战略投资,和绝味食品共同出资1亿元。这是京东战略投资部门在河南的首单股权投资。所谓战略投资,不是简单拿分红,而是要合伙抢地盘、搞生态。
对于千味央厨和零售大佬的动作,三全看在眼里,急在心里。
那些年,三全在生鲜预制菜赛道上屡战屡败。自己的失败固然可恨,朋友的成功更令人揪心。(三全新掌门陈泽民之子陈南和李伟是好哥们儿)
2019年,三全在“锅圈食汇”A+轮融资中出资5000万元。
你拉帮结派,我也要扶持小弟。
锅圈食汇是河南的火锅预制菜品牌,但和千味央厨路子不同,它不是中央厨房,而是个新零售企业,在社区附近开店,主打一站式火锅食材采购。
锅圈食汇的发育逻辑是通过加盟扩张门店,用渠道权换得对上游企业的议价权,从而完成供应链的垂直整合,类似于我们前面写过的《零食大战这八年》中的量贩零食业态。
战况胶着时,全球公共卫生事件爆发,预制菜进程突然加速。
餐饮店个个被揍得鼻青脸肿,火锅界老大海底捞2020年净利润暴跌90%,餐厅关闭导致的一次性资产处置损失、减值损失就超过36亿元,正餐界老大西贝的日子也很艰难,老板贾国龙则在采访中透露,西贝账上的现金加贷款只够撑三个月。
在这种情势下,年菜、外卖、团餐、居家消费顺势崛起,带火了预制菜。
海底捞推出了“开饭了”系列,锅圈食汇在全国开了近一万家线下店;安井食品推出预制菜“冻品先生”“安井小厨”两大预制菜子品牌;国联水产和上海日冷集团合作进军预制菜;格力电器、长虹美菱、美的集团启动了预制菜装备业务;京东、顺丰推出预制菜物流供应链计划;盒马鲜生、每日优鲜、叮咚买菜等新零售玩家,也都在加速布局预制菜。
2023年,“培育发展预制菜产业”首次写入中央一号文件,这个在中国已默默发育多年的行业,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。
当时中国预制菜渗透率不到10%,日本高达60%,资本赶紧画饼,说预制菜未来增长可期!厚生、红杉、高瓴等头部机构闭眼冲,预制菜经济开始暴走,根据企查查数据,2021年预制菜行业共完成28起融资事件,全年披露融资金额超过30亿元,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。
二、预制菜的底层逻辑
那么,预制菜到底是一时热潮,还是一种必然趋势呢?
我和一位宁波读者交流时,他对预制菜提出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疑问。我们就从他的问题入手,来剖析这个行业吧。
这位读者出生在宁海县,从小特别爱吃肉包子,在肉包子品鉴上颇有心得。他说宁海县最好吃的包子店,叫老章包子,都是手工现包。在他儿时的记忆里,食客们总是在热腾腾的香气中,争相排队购买,将整个一楼围得水泄不通。但后来老店被拆迁,分成了几家小店,虽然味道没变,但也再没有昔日的盛况。
在外工作时,宁波读者到处寻找好吃的包子店,却再也找不到小时候的味道。他说在广州这种大城市吃到的肉包,明显感到是由食材边角料、经工厂流水线做出来的。
宁波读者问,为什么优质的手工包子铺做不大,在大城市也看不到?
一个餐饮店是否具有扩张潜力,根本上取决于两点,一是成本控制能力,二是菜品标准化能力。
菜品标准化很好理解,假如老章包子开了一堆加盟店,但每个店味道都不一样,消费者就无法形成品牌认知,也就没人会再来加盟了,老章要么固守城池,要么被扩张性更强的包子铺挤垮。
解决标准化的最佳方式是建中央厨房,但工业化流水线必然造成口感损失。
下过厨房的人,都知道机器和人工的差别有多大。
我家包饺子时,需要一边搅馅料一边掺水,让空气和水分进入肉团,这样吃起来才会松软多汁,绞肉机绞出来的肉馅,就更像是一坨肉丸水泥。
如果老章不想牺牲口感,那么他就不得不放弃机器,聘用大量员工来和面、搅馅料,就和《水饺皇后》里一样。
早期的中央厨房,还真是这么操作的。但随着机器效率的不断提高,人工成本不断上涨,门店规模的不断扩大,这条路就走不下去了。
这就来到了更复杂的成本控制环节。
食材、租金、人工,是压在餐饮老板头上的三座大山,现在还得加一座“外卖抽成”。这些成本大头不断攀升,导致传统餐饮越做越累,越做利润越薄。
举个例子,小仙在成都非核心地段,开了一家普通小炒店,每天进账2000块,一个月就是6万块,买食材花了3万块,每月铺租3000块,水电燃气费2000块,包装耗材、外卖平台抽成5000块,帮厨5000块,再加上10万左右的门面转让费、装修设备摊销费,小仙每天四点起床备菜、12点刷锅洗碗,一个月可能赚不到一万块。
做餐饮的读者,看到这个算法可能要骂人,因为照此计算,小仙的净利润率居然达到了16%,比西贝还高。
根据2020年2月1日贾国龙接受投中网采访的信息,西贝2019年单日营收2000万,一年就是72亿元。其中原材料、人工成本、铺租及各种税收占总成本的比例,分别为30%、30%、10%和6%-8%,西贝净利润为9.6亿,净利润率为13%。
由于拥有强大的渠道议价权,而且采用大量预制菜(此处采用老百姓心中的定义),西贝的原材料成本只占30%,在餐饮店中真的属于极限操作了。
但是,西贝的店都是开在黄金地段、黄金铺位,铺租成本高。
西贝的另一成本大头是人工。西贝主要在大城市开店,而且为了增加观赏性,还把揉面老阿姨换成了揉面小姐姐,这些策略无疑都会提高人工成本。
2020年初,西贝每月要付高达1.56亿元的工资,加上5200万房租,至少是2亿,贾国龙每天一睁眼就要花670万,遇到点事儿,能不急得火星子直冒?
以西贝的烧钱速度,根本不可能采用大量现炒。这不仅仅是食材成本的问题,而是聘请大厨实在是太贵了。
猎聘网上,上海的中餐行政主厨月薪2万起步十分常见,北京也多在1.5万以上。西贝厨师只会操作微波炉+电磁炉,确实没有技术含量,但人家胜在便宜。
根据网友贴出的西贝招聘广告,西贝厨师工资只有5000到7000元,上限还没有服务员高。

西贝招聘广告
但这个工资支出,已经让老板十分肉疼了。
贾国龙2024年在一场餐饮产业大会上感叹:“36年前的1988年,我在内蒙古临河这样一个小城开始做餐饮,记得那时候工作人员的工资才是四五十块钱,180元就可以聘一个经理,厨师长的工资是300块钱……现在他们的工资基本是当时的100倍。”
如果西贝撤掉预制菜,食材成本将会上浮15%到20%;再全部换上大厨,西贝的单店利润分分钟跌破10%,最后没有活路。
西贝的困境,不单是它自己的困境,也是这个时代所有餐饮店的困境。
我亲戚开过小餐馆,没请外人帮忙,每天天不亮就要买菜、备菜、提前熬制汤汁,晚上九点打烊,收拾完十一点,披星戴月地忙活了半个月,发现还不如去上班,就关门了。
新都区有一家好吃的蒸牛肉,每到饭点,老板忙不过来,总是怒目圆睁,讲话也十分暴躁。有次一个食客见老板火气太大,便用成都话柔言细语地建议“多请几个人嘛”,只见老板听完更暴躁了,黑着脸,重重地把蒸牛肉扣在桌子上,一副你再说我就要打人了的样子。
餐饮人动不动就崩溃,是因为预制菜出现之前,做餐饮真的是一件痛苦且利润微薄的事。
大家可以回忆一下,二三十年前赚钱的餐饮店,是不是都是大酒楼?
西贝一代店基本都开在城市边缘,单店至少上千平方,当时在北京开店的海底捞,同样是上千平方,不像现在多是三百来平方。
在传统餐饮时代,铺租和人工还不算贵,只有面积如此大的餐饮店,才能提供足够的后厨操作空间,足够的营业空间,从而提高坪效比和单店利润。
当时一些餐饮店已经开始尝试自建中央厨房,但因为铺租和人工成本尚可承受,传统的盈利模式尚能持续,改革动力并不算足,预制菜也就没有得到快速发展。
2011年后情况变了,城市的铺租越来越贵,人工成本飞速攀升,逼迫餐饮企业砍掉后厨空间和人员,自建中央厨房,预制菜成为大势所趋。
大商场和购物中心的崛起,也深刻改写了餐饮店的盈利模式。
西贝曾把一代店直接照搬到商场内部,但很快就被不断狂涨的租金狠狠教育了,只好改革店型。西贝今天的店型,过去可能只是西贝的厨房大小。
后厨空间的压缩,使西贝不得不把一部分食材的加工环节挪出门店,自建中央厨房。
根据《人民周刊》2019年的一则采访,一位著名餐饮人表示,餐厅毛利60%,人力、租金成本约30%-40%,管理成本10%。要做到净利率10%,就得精打细算,否则倒闭概率很高,这就逼迫餐饮从后端(生产和供应链环节)节约成本。
一句话,时代变了,只有大量消灭传统厨师,餐饮店才有得活。
老章包子被拆成小店后,为什么没有重新租门面,做回大店呢?因为铺租和人工成本变高,过去能赚钱的生意,现在不再赚钱了。
所以,预制菜本质上是一场餐饮业的降本增效革命,通过整合供应链,注入现代食品加工工艺,大幅度缩减后厨的操作时间和人力,提升翻台率和外卖能力,最终提高单店利润。
这两天,西贝赠送了大量打折券,门店又开始排队了,还顺便带火了信息透明化走在前列的老乡鸡,以及主打“穷鬼西餐”的预制菜王者选手萨莉亚。
消费者相当门儿清,黑后厨的食材质量,远不如大品牌的中央厨房和预制菜。只要信息透明,价格符合预期,大家愿意接受预制菜。
三、艰难崛起
尽管预制菜崛起具有必然性,但这个产业过去在中国却走得异常艰难。
判断一个行业处于什么阶段,一看增速,二看竞争格局。
萌芽期,几个先行者吃到了肉,打下了些许地盘。
成长期,大量模仿者为了抢肉吃,肉搏上阵,菜鸡互啄,狂打价格战,行业增速极快。
成熟期,经过几轮血洗,小弟们残的残,死的死,龙头大佬出现,增速放缓。
美国、日本的预制菜渗透率高达60%以上,垄断特征突出,尤其是日本,一家日冷集团的市占率就超过了20%,处于成熟期。
综合各机构研报数据,过去几年,中国的预制菜行业的增速在20%以上,渗透率仅为10%,竞争格局极其分散,像双汇、安井这样的龙头企业,市占率也不过2%左右,处于成长期。
预制菜和餐饮连锁化率呈高度正相关。根据平安证券研究报告,2022年加拿大、美国和日本的餐饮连锁化率分别为64%、58%和56%,中国的餐饮连锁化率仅为18%。
这个数据和现象,其实很奇怪。
快餐业进入中国,仅仅比进入日本晚了十年。从第一家肯德基在北京开店算起,连锁快餐业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近40年的历史。以中国人的学习速度,有这时间光刻机都造出来了,所以不是不想,而是臣妾做不到。
出现这种发展差异的根源在于,美国和日本的政治经济被少数富豪或财阀集团控制,中国既没有控制国家命脉的财阀大亨,也没有食品游说集团,私人食品集团的政治影响力极其有限,因此中国餐饮业完全是市场自由竞争的结果。
当自由竞争遇上中餐标准化,就构成了一个世纪难题。
第一个问题,选择什么菜来进行标准化?中国物产极丰富,美食文化极深厚,地域特色极突出,日本、美国本来就没什么好吃的食物,炸鸡、拉面已经是顶级美食了,但放到中国就显得很普通。所以,没有一款单品能统一中国人的胃口。
第二个问题,中餐是门玄学,一个“盐少许、辣椒适量、大火快炒”的神秘配方,就够研发团队琢磨半天了。
第三个问题,中餐的炒菜讲究锅气,而锅气基于爆炒瞬间的美拉德反应,虽然现在有锅气香精这种玩意儿,但我去看了不少博主测评,加了锅气香精后,菜品的确会有锅气的香味,但仍然没有锅气的口感,反而越吃越别扭。
餐饮店如果想追求锅气,就得重回依赖大厨的老路上。但我们已经分析过,这条路成本高昂,只适合高冷的小而美路线,根本无法扩张。
所以,中国最早做出标准化大单品的餐饮连锁,都是不需要大厨,操作“简单粗暴”的细分业态,比如奶茶、面点面食、中式火锅。
奶茶最容易实现标准化,供应链整合难度最低,连锁化率最高,达到了55%。
其次就是中餐扛把子火锅。
火锅是中餐连锁化率最高的品类,市场规模在川菜、粤菜、江浙菜之上,而又以川渝火锅势头最大。
火锅能够在八大菜系之外独树一帜,根本原因不是中国人多爱吃火锅,而是标准化难度低,基本只需要解决底料炒制和食材保鲜问题,完全不依赖厨师。
说个冷知识,中国火锅品牌的发家地,不是川渝,而是北京。
根据川渝老辈子的回忆,作为火锅界顶流的川渝火锅,在80年代之前并不盛行。因为过去缺肉缺油,民间根本不可能形成吃高油脂高肉类火锅的习惯。
实际上,当时北方吃火锅更多,北京才是初代火锅之都。
老北京人爱吃的涮羊肉,是八旗从关外带到北京的,乾隆就是个重度火锅爱好者,史书记载他一个月里吃了60次火锅。
北京是最早引进肯德基等西式快餐业态的城市,也最早诞生餐饮连锁业态,当时上海著名餐厅荣华楼,还专门到北京学习做西式炸鸡和连锁化。
90年代后期,百年老店东来顺开始连锁化经营,呷哺呷哺、小肥羊也先后到北京开店发家,全国各地的火锅店聚集京师,接着从北向南打,在西南引爆业态,以海底捞2004年在北京开店为标志,川渝火锅反向输出一波,占领全国市场。
海底捞在北京开店时,人均消费只有六七十元,在北京属于中档火锅的价格。当时北京的火锅市场已杀得一片血红,内蒙古的小羊纷纷惨遭毒手,羊肉常年维持在15元一盘左右,餐饮界断言,北京的大多数火锅店活不过三年。
为了抢客人,海底捞提供了极致周到的服务,北京人很吃这一套,到2010年,海底捞就在北京开了20家火锅店。
因此,北京才是中国火锅品牌的发家地。昔日的“中华火锅第一股”小肥羊,今天的火锅霸主海底捞,都是在北京实现连锁化的梦想。
火锅的另一大优势是成瘾性强,就和炸鸡、奶茶、咖啡类似。
成都地铁有个魔性广告,“不ci火锅,就ci烤匠”,就是强调火锅和烤鱼的成瘾性。
缺乏成瘾性和特色的餐饮品牌,哪怕背景再强,在中国也很难存活。
百胜中国2004年曾收购中式餐厅东方既白,并设想将其打造成“中式快餐全球品牌”。然而,在供应链体系、资金、人员的全面优势下,东方既白依然被揍得体无完肤,直到2022年终止运营。
原因是没有特点。
东方既白菜品极多,最多有200个,饭、粥、面、包子、豆浆、梅菜扣肉饭、糖醋小排餐样样都有,但缺乏记忆点。
西贝最初也有一百多个单品,但因为供应链复杂,成本居高不下,转而采取革命性的大单品模式,把菜品精简到45个,倒逼团队打造出羊肉串、西贝面筋、浇汁莜面等数个年销售额过亿元的爆款单品。
2012年以后,中国餐饮连锁化进程加快。一批信奉“标准化+单店效率”的中式连锁餐饮玩家,老乡鸡、大米先生、大碗先生、费大厨、兰湘子,在摸索中默默崛起。
一些连锁餐饮店为了实现更大规模的扩张,选择自建中央厨房。其中一些企业的中央厨房被养得特别大,产能远超企业所需,于是放开了对外营业,变成专业的预制菜企业。
最典型的就是蜀海供应链和颐海国际。
蜀海、颐海,早期都是海底捞的供应链分公司,分别给海底捞供应新鲜菜品和火锅底料。海底捞的快速扩张,为蜀海和颐海提供了充分的养料。后来这两家公司先后独立,既给海底捞供货,也给其它连锁餐饮店供货。
目前蜀海SKU数超过5万个,2018年销售额50亿,是太二酸菜鱼、黄记煌、船歌鱼水饺、大米先生等著名餐馆的供应商;颐海2024年营业额65亿,2020年预制菜股暴涨那阵,市值一度突破1000亿港元,目前是中国第二大复合调味料生产商。
海底捞的成功自然让西贝眼红。
2015年起,贾国龙就致力于孵化快餐品牌,先后推出西贝莜面工坊、麦香村、西贝超级肉夹馍、贾国龙酒酿空气馍(后改名贾国龙中国堡)、贾国龙小锅牛肉等11个快餐品牌,2018年在呼和浩特投资6亿建中央厨房和配送基地,2019年推出预制菜品牌“贾国龙功夫菜”,但这些尝试都折戟沉沙。
除了海底捞、西贝这样的餐饮玩家,还有圣农发展、温氏股份这样的生鲜肉制品玩家。
根据《2025年中国预制菜企业100强》榜单,中国排名前十的预制菜企业中,有七个是从事养殖和加工一体化的企业,分别是双汇集团、温氏食品、圣农发展、新希望、金字火腿、得利斯、国联水产。
这些上游的农林牧副渔企业,本身具有原材料和冷链优势,转型预制菜的试错成本更低。
更重要的是,它们面对餐饮巨头没什么议价权,一直都干着最苦最累的活,赚着最低的利润,承担最大的波动性风险,几乎是含泪咬牙切入预制菜的。
圣农发展从养鸡场起步,1993年成为肯德基的供货商,接着成了麦当劳、塔斯汀、德克士、沃尔玛的核心供应商,业内称号“亚洲鸡王”。
但养鸡杀鸡这门生意,实在太苦逼了。
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,我国2021年商品肉鸡养殖平均收益为0.56元/只,每养一只鸡,只赚五毛钱!所以圣农并不甘心当餐饮巨头背后的马仔,而是要自己成为一个上中下游通吃的巨头。
圣农2003年成立了一家叫“圣农食品”的独立公司,孵化预制鸡肉熟食,2006年推出自有餐饮品牌美其乐汉堡,发育十分迅速,后并入圣农。2018年圣农在天猫、京东首开旗舰店,销售预制鸡胸肉,2020年推出了脆皮炸鸡、滋滋烤翅、霸气手枪腿等爆款单品,填补了生鸡价格萎靡的亏空。
和圣农类似,温氏股份的传统业务是养殖和销售猪/鸡肉,但旗下子公司温氏佳味在2004年就切入预制菜赛道,先是和大润发、陶陶居、老乡鸡等大客户合作,2021年推出了胡椒猪肚鸡汤、椰子鸡、口水鸡、梅菜扣肉等自有预制菜产品。
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,越来越多的玩家加入了这场游戏。根据企查查数据,预制菜相关企业的新增注册量,从2011年的不到2000家,增长到2020年的1.2万家。注意,这还只是新增,不是总数。

预制菜产业原本只是在默默发育,但2020年因为全球供应链危机,这条赛道加速爆发了,不但进入了资本视野,更进入了政策视野。
2022年,广东、河南、山东、四川等农业渔业强省,都分别出台了专门文件,引发各自的标准体系,支持预制菜产业发展,激烈争夺话语权。
中国预制菜企业,由此演化出四大类型。
第一类,食品界老辈子,依托原材料、加工技术和冷链优势,很早就开始孵化预制菜,比如前面讲到的三全、思念、圣农、温氏、双汇。
第二类,连锁餐饮扛把子,它们依托自有的中央厨房体系,丝滑转型预制菜,比如海底捞、西贝。
第三类,新零售企业,它们直接和消费者打交道,凭借强大的渠道优势和冷链物流优势,直接杀进预制菜,比如锅圈食汇、叮咚买菜、每日优鲜、盒马生鲜。
第四类,专门生产预制菜的企业,比如千味央厨、味知香,甚至各种新成立的小作坊。
还有一些和食品行业没有任何交集的企业,比如昔日的“鞋王”贵人鸟,昔日“宇宙第一房企”碧桂园,也布局了预制菜。
我开始也不理解,但一去查它们的股价,瞬间就懂了。
研报显示,2023年,中国预制菜市场规模已超过5100亿元,同比增长23%,有望在2026年突破一万亿规模。
压抑已久的预制菜经济正欲喷薄而出,隐忧却不断显现。
四、降温刹车
最近,在德国留学的陈希(化名),被自称卖中国预制菜的二道贩子宰了一刀。
在德国超市,预制菜十分常见。陈希一位德国好友,有个89岁的独居姥姥,一直以来全靠吃预制菜为生。
陈希说德国预制菜大都需要烤制,口味不太适合中国人,所以她想买点中国产的预制菜,因为物流问题去找了个二道贩子,但对方先是虚假发货,后来直接联系不上了。
另一个在韩国工作的读者也被坑过,国内5块钱一袋的预制菜,预制菜二道贩子卖了他15块。
中国每年有上百万海外留学生,世界各地有6000万华侨华人,由于中国预制菜在国外面临关税、物流、渠道、法律等多重关卡,他们想吃家乡的预制菜还吃不上,成了无良商家打歪主意的对象。
而且这些预制菜能够实现无冷链国际物流运输,可想而知有多么依赖防腐剂。
认真做预制菜的企业,还在投入重金自建冷链,研发锁鲜技术,小作坊却凭着“科技与狠活”,得到了迅速扩张,难道不是劣币驱逐良币?
究其原因,是因为缺乏国家统一标准,地方各自为政,行业野蛮生长。
2023年9月,教育部公开表示,对“预制菜进校园”应持十分审慎态度,央视更屡屡曝光预制菜黑作坊。
既然预制菜在中国名声不好,国家为什么不对其狠下死手,反而是支持发展呢?

其实,我们看看预制菜的产业链,就很容易想明白了。
预制菜的上游是原材料供应,和农村经济紧密相连;下游是餐饮企业和消费者,和食品安全息息相关。
预制菜最先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。熟悉政策的读者应该知道,自2004年以来,每年一号文件都聚焦三农问题。因此,预制菜首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抓手。
预制菜产业链长,有了一家龙头,就会吸引一大批上下游企业,形成产业生态,解决大量就业。
比如开封某县过去三年建了76条酸辣粉生产线,为了解决原料问题,又引进了一家淀粉厂,投产后能消化周边300公里内全部的土豆和红薯,一下子就把农民收入和工厂降本的问题解决了。
所以国家为了通盘考虑,让农民、消费者和守规矩的企业获利,让不守规矩的企业出局,先是给到了支持性的一号文件,紧接着商务部、市场监管局等部委就出台规范性文件,希望它争口气,健康地发展下去。
国家在这时候踩一脚刹车,也正当其时。
由于这几年预制菜行业的扩张过于激进,内卷严重,毛利率不断下滑,给产业链埋下了大雷。
据不完全统计,国内预制菜相关企业超过7万家。
一个行业拥有7万家工厂,说明价格战极为残酷,利润空间被不断压薄,大部分工厂处于价值链底端。
可这7万家工厂,又涉及数百万个就业岗位,是极为重要的就业蓄水池,以当前的就业形势,这个产业对国家和社会意义重大。
河南某预制菜大县的预制菜创新示范产业园,维系着3万名农民的饭碗,一旦产业停摆,将对当地经济造成灾难性的打击。
据媒体报道,某龙头品牌的批发价格显示,一包250g黑鱼片只卖7.2元,一包1KG的麻辣肉片只卖14元。
大家逛超市的时候,是不是发现黑鱼片、小龙虾便宜得离谱?原因就是这几年预制菜行业的高烈度竞争。
据同花顺数据,中国预制菜上市公司的毛利率整体呈下滑趋势,从2018年的20%降至2024年的14%左右。

如果企业因为过度内卷,导致突然大量倒闭,对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不是一切归零,而是回到负值。因为过剩的产能,积累的债务,流水线上的工人,乃至上游种地的农民,都不是可以一键撤回的。
2024年3月,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《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》,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预制菜的定义。
这个动作,就是为了降温、调整、再出发。
根据该通知,预制菜不允许添加防腐剂,不包括主食类食品,不包括可直接食用的蔬菜(水果)沙拉等凉拌菜。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,不属于预制菜。
说实话,国家定义的预制菜,并不是老百姓心目中的预制菜。但这条不太完美的新定义,仍然有个重大进步,那就是明确了预制菜不能添加防腐剂。
淘宝上一搜,食用级防腐剂卖三百多块一箱,一箱25公斤。按照国家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,每公斤肉的防腐剂用量为0.5到1g,按一袋200g预制菜80g肉计算,三百多块的防腐剂,可以搞出30万袋预制菜。
这还是比较好的食用级防腐剂,如果黑心商家换成工业防腐剂,那就更便宜了。
而自建冷链,成本就高昂得多。
根据某冷库商家的报价,一个5000平方的大型冷库需要450万,这还不包括土地拆迁费、电费、人工费、冷冻车购买费。
良心厂家要花几千万甚至数亿元搞定的事,小作坊几百块就解决了,这才是最大的不公平。
新规出台大大提高了行业门槛,将会逐步清理小作坊、黑作坊。
通知发布后,预制菜企业的注册增长率,便从2023年的683%骤降到2024年的147%。随着后续监管体系的完善,必然会进一步加速行业出清。
结语
预制菜的狂飙与刹车,并非一个简单的行业周期,而是中国餐饮工业化进程中的一次深度校准。
预制菜的终局,并非取代传统厨艺,而是推动一场深刻的分工。
未来的餐饮图景将日益清晰:一端是极致效率化的“工业厨房”,通过标准化预制,服务于对便捷和性价比有高需求的快餐、外卖和家庭备餐;另一端则是极致体验化的“手工厨房”,以现场烹饪的“锅气”和厨师的创意,服务于追求社交、品味与独特体验的消费场景。
在这场价值重构中,大浪淘沙,始于监管,终于价值。
当潮水退去,我们终将看清谁在裸泳,而谁,又真正为中国人的餐桌,构建了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价值。